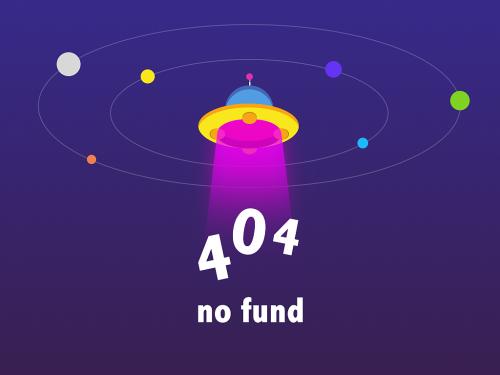朴素的政治,朴素的文明
1942年,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,苏德战争相持不下,中国的抗战,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。世界历史的大转折,就此开始。
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,即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文明,为什么会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、落后挨打的境地。中国的历史何以兴衰更迭,而绵延的中华文明,何以会陷入周期性的腐败?
那时的蒋介石也在思考这同样的一个问题,他率先给出了答案。
1943年,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《中国之命运》。抗战期间的蒋委员长在重庆正襟危坐,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——他从明代的崩溃开始反思中国历史。
学术界有一种说法,即“崖山之后无中华”,也就是说,南宋被蒙古所灭后,中华文明就衰落了。在蒋介石看来,今日之中华民国决不能重蹈明亡之覆辙,故当务之急,就是找到明亡的原因。
蒋介石认为:明朝灭亡的原因,则是因为它“一败于外寇,二败于流寇”,即一败于满清,再败于李自成。他指出,当今之中国同样也是如此。当今之“外寇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,而所谓“流寇”究竟是谁,则不言自明。
那么,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,而明朝怎样才能不亡呢?1940年,钱穆在《国学大纲》中这样说:“若先和满,一意剿寇,尚可救。”而傅斯年也认为,明朝要避免灭亡,那就必须采取“先和满,再剿寇”的政策。这就是中国当时“大儒”们的意见,它与汪精卫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,这无疑就是说:国民党应该先与日本妥协和谈,然后一意消灭共产党。
蒋介石在《中国之命运》中所阐释的,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种主张。蒋介石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乃至“共识”,代表了中国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。1944年,是明亡三百周年,自1942年以来,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,来思考中国衰亡的原因,以寻求人类的出路,这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话题。
当时的中国思想界,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“大儒”们公开唱反调的,只有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郭沫若认为,明既非亡于“外寇”,也非亡于“流寇”,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。他的文章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。
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究竟有多腐败呢?仅从其货币政策上,便可以清楚地看到。
1942年,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,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,于是,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,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。随后基于形势严峻,美国于1942年2月2日,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。国民党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,来华生利,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,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,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、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,此即所谓“发国难财”一说的由来。
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要对这笔“国难财”征税,此论一出,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,他感慨地说: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“天下为公”的宗旨,实际执行的是“地上为私”四个大字。
郭沫若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里的名言是:面对天下饥荒,人民陷入水火,“聚敛”的是官家,而“救灾”的却是“寇家”,于是,朝廷是在“用兵剿寇”,而百姓却是“望寇剿兵”,人心所向,明朝必亡。文章发表之后,国民党当局却立即组织叶青、陶希圣等在《中央日报》撰文,予以高调鞭挞,1946年2月,蒋介石手下的特务,在校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。
1936年10月,鲁迅病逝于上海,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:孔子之前,无数孔子,孔子之后,一无孔子;鲁迅之前,一无鲁迅,鲁迅之后,无数鲁迅。”
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,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:您的文章,大有益于中国人民,只嫌其少,不嫌其多。
平心而论,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。他的秘书中,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,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,一个是陈布雷,一个则是徐复观。
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六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,以督察八路军之军政。1943年5月,徐复观以18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,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。回到重庆后,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,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,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“整风运动”,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。
他说,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。第一个不同,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,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,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。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,恰就在于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,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。他认为,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,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,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。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。因为“国民党的组成部分,已经完全是传统的、脱离了广大群众的知识分子,这种知识分子,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,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……要以广大的农民为民主的基础,一切政治措施,应以解决农民问题、土地问题为总方向、总归结。”
在延安期间,徐复观与毛泽东有5次长谈,每次谈话都是向毛泽东请教历史问题,因此得到了“延安精神”的真传。徐复观的报告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,将他写的这份报告批转国民党要员们认真学习,报告上布满了蒋介石的圈点和评语。
其实,蒋介石知道国民党腐败,他也知道国民党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。他知道共产党廉洁,他也知道共产党的法宝不仅仅是廉洁。
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5月到延安,他亲眼看到了延安的情况,不禁发自肺腑地说:我一向以为,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,现在我才知道,这个人已经出生了,而且已经50多岁了,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。
对比国民党统治区,陈嘉庚先生感慨地说,延安有“十没有”:“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,二没有土豪劣绅,三没有赌博,四没有娼妓,五没有小老婆,六没有叫化子,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,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,九没有人吃摩擦饭,十没有人发国难财。”当时的延安实在是太穷了。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之下,延安穷得连毛泽东也是一日两餐,两餐又常是一稀一干,基本没有菜。就是这样一个大家连饭也吃不饱的延安,却被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仁人志士视为“圣地”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
延安没有物质生活的腐败,延安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,而这就是延安作风吗?这就是使延安成为“圣地”的原因吗?在毛泽东看来,这还远远不是“延安作风”的实质。延安的朴素不仅是物质上的朴素,而是精神上的朴素。延安代表了朴素的文明,朴素的政治,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。
要避免中国和中国文明陷入周期性腐败,那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:第一,是中国历史上,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的问题。第二,是中国社会领导力量在精神和思想作风上的贫乏、无能、懈怠和麻痹问题。在毛泽东看来,物质生活上的腐败,那只是“看得见的”腐败与堕落,而更加危险的腐败,却是思想方式的腐败、行为作风的腐败、乃至于说话方式——文风的腐败。中华民族若要真正地在灭顶之灾中警醒,那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样的腐败。
“往事越千年。”毛泽东就是这样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,总结了中国天下兴亡的周期律,而他把中国的历史,概括为朴素战胜腐败的历史,实干战胜虚文的历史,艰苦奋斗战胜贪图享乐的历史。
中国开化最早,文明领先,但是,这样的文明古国,却反复地被那些“蛮夷”们打败了,而这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?毛泽东说,这里的根源,就在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于“文明”的形式主义理解。
文者,纹也。在中国历史上,文明被理解为雕饰,正是对于这种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追求,束缚了“文明化”的中国人,使他们对于“文明”的追求,脱离了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。那么,什么是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呢?毛泽东说,这就是战斗与生产,就是“又战斗来又生产”的广大人民群众。
毛泽东认为,儒家之所以不能代表中国文明,就是因为儒家对于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,它认为文明就是“礼仪”,而在当时,这种礼仪就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度,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明,造成了中国的分裂。
毛泽东反对儒家而推崇墨法两家,乃是因为墨家与法家的思想,是建立在生产与战斗的基础上,在毛泽东看来,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,儒家追求的不过是文明的形式而已,而墨法两家,追求的则是文明的实质。
在毛泽东看来,对于形式主义的文明的追求,在六朝时期达到了高峰,而舍本逐末的结果,必然是求荣取辱。他认为,“文风”的问题,就是作风的问题,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。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,固然是贵族和豪族,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,同样是贵族和豪族。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,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。”这里的意思毋宁是说: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,不是靠文采、靠风骚,靠舞文弄墨得天下的。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,英勇杀敌,而不是文采和风骚。
中国文明悠久,宋代以降,随着出版业的兴盛,读书人成堆。但是,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,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,在意志力方面,中原的士大夫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,就是文明的异化。
而毛泽东青年时代《致黎锦熙信》中说过:中国士大夫一贯“以读书为上,办事为下”,以为“农、工、商业”,皆为小人之学,系为小人所设,而“大人”所不为也。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,“而世上经营,遂以多数为标准”。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,士大夫的知识,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。在毛泽东看来,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,而北方的夷狄,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。
16世纪以降,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: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、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,那个文明的主体——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。因此,重视生产、科技和实践,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。与之相对,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、鄙视实践,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。于是,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,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,因而,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。
重建中华文明 重建中华政治
中国的士大夫阶级,从根本上忘记了四个字——实事求是。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: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、人类文明演讲的历史,也就是“文明的实质”——战斗与生产,战胜“文明的形式”的历史,就是那种脱离战斗与生产的文风、作风和学风遭到武器的无情批判与淘汰的历史。所谓“实事求是”,就是从战斗与生产中去寻求文明的实质。这个逻辑,毛泽东坚持了一生。
1964年2月3日,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:“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,摧残青年,我很不赞成。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,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、大学,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,大约是个吹鼓手。人家死了人,他去吹吹打打。他会弹琴、射箭、驾车子,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。开头做过小官,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,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。他后来办私塾,反对学生从事劳动。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,才写了《本草纲目》。更早些的,有所发明的祖冲之,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、大学。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,也卖过报。他是电的大发明家。英国的瓦特是工人,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。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,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。”
在毛泽东看来,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,害了中国文明,毁灭了华而不实的士大夫阶级,而这种学风、作风和文风的腐败,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。
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,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,至1940年减少到3万余人,抗战开始后,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,陕甘宁边区有知识文化人约4万,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,延安处处有学校,成为了著名的“文化城”。
然而,要复兴中华文明,仅仅靠读书是不行的,因为那就必须根绝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,就必须把文明建立在生产与战斗这个实质之上。而所谓“艰苦奋斗”,无非是说:“文明”绝非表面的文饰,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,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,伟大的文明,就是埋藏在行动(生产与战斗)中的朴素精神。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,这是血的教训,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,是撬动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杠杆。
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和“实事求是”,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。
毛泽东指出,要重建中华文明,要重建中国政治,就必须从三个部分入手。
首先,“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”。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,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,而是理论脱离实际,生活脱离群众。知识脱离实际,学术脱离政治,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。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学风问题”。
而“学风问题”由来已久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毛泽东说:什么是知识?难道读了几本书,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?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?
毛泽东的话,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,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:
什么是知识?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,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,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,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。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,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,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。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?没有了。
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,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,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?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,毕业了,算有知识了。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,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,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,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?我以为很难,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。
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?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: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,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,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。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?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,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,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。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,但是必须知道,就一定的情况说来,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,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,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。最重要的,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。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,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,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,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。
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?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,变为实际工作者,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。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。
所谓“主观主义”,其在学风上的表现,也就是理论脱离实际,其根源,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、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。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。因此,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,首先就必须首先在读书人中反对“主观主义”这种学风。其次,必须反对宗派主义。
在中国历史上,“宗派主义”的另一个说法,其实就是“朋党”或者“党争”。
所谓“朋党”大盛于北宋。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《周礼》,于是,这就使得熙宁以降,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争论,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。欧阳修做《朋党论》,他便以为“君子”们争的是“大义”,而“小人”争的是利禄,故“小人无朋,惟君子则有之”。
然而,正是“党争”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,“党争”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故雍正在《御制朋党论》中说,“朋党”就是结党营私,其名曰追求“大义”,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。对于官员而言,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,置于国法之上,置于道义之上,党争是大私,是官场痼疾,党争一日不去,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。
毛泽东认为,中国共产党名曰一党,而实质上没有党派的利益,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:
“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: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,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。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,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。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,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,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?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,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,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。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,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,甚至排斥他们。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……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,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,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,应当同时并进。”
而第三个要反对的,就是“党八股”。所谓“八股”,就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。毛泽东认为,中国有两个八股,一个是旧八股,一个是新八股或者“洋八股”,而“新八股”、新教条是“五四”的产物,它向右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,而向左则发展为党内的教条主义,即机械地、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。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,不仅是要打倒封建主义、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,也要打倒党内的教条主义。而这在文风上,就必须同时打倒旧八股、洋八股和党八股。
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,对于什么是知识、什么是“文明”的错误理解,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,不仅害了中国文明,不仅害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,也害了中国共产党,害了中国人民。它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,党内的错误思想,既是中国历史糟粕在党内的反映,也是这种糟粕在“五四”传统中的反映。当然,毛泽东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,批判地总结“五四”以来的中国现代史,是为了批判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是为了批判长期统治中共的王明路线。
1939年,刘少奇为马列学员做了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演讲,他认为:诸如王明这些人虽然读了点书,但他们的问题是修养不够,他们在精神境界上不但不能望马克思、列宁之项背,而且离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也相差千里。在毛泽东看来,王明等人之所以修养不够,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养。他们自以为读了几本苏联的书就可以号称有马列主义修养,他们根本就不懂得,一个人的修养,只能从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,只能从人民群众中来,离开了这个实质,就无所谓共产党人的修养。
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方式,那就是通过妆扮成某种学说、思想和“真理”的合法继承人,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和统治地位,这就是所谓通过垄断“意识形态霸权”以施行统治——毛泽东和安托尼·葛兰西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这种统治方式。而王明在党内所要确立的,就是这样一种统治。
年青的王明在中共党内本无资历,而他掌握的最大的资本,就是思想理论的资源,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,是斯大林的“钦差大臣”,此人记忆力甚好,他用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俄文,对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,能够倒背如流。
高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旗,王明做出的却是诛心之论。戴震的名言是:今之儒者,“以理杀人”,而王明就是这样的“今之儒者”,王明的肃反,就是“以理杀人”。
对于王明的“厉害”,对于王明的肃反,中共党内是记忆犹新的。
1937年11月20日,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,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恭迎,陕北公学大操场万人欢呼。而毛泽东说,这是“喜从天降”。但这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般态度。高岗后来则愤愤不平地这样说:“什么喜从天降,是祸从天降!”
“无事家中坐,祸从天上来”——王明的再次“自天而降”,的确不能不使人忆起1931年1月米夫等人给中共“空降”下来一个党中央。而这一次,王明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,同机到达的还有康生、陈云、曾山、孟庆树(王明的夫人)。
1937年12月9日至14日,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,王明、康生、陈云立即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,与张闻天、毛泽东组成“五大书记”,王明虽然没有被推为“总书记”,但他却在会上表现得不可一世——王明那时的气势,甚至超过了初出茅庐时的六届四中全会。
“12月会议”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七大,1936年12月7日,毛泽东当选中革军委主席,1938年6月11日,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,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,会议通过了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决定。正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受命返回中国,传达会议决定。行前,季米特洛夫特别叮嘱他说:“应该告诉全党,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,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。其他人,如王明,不要再争领导人了。”
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,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,任命王明为中央统战部长、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。然而,王明却继续采取攻势,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,王明请他主持公道,提出要让全党一起来评理,而王明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: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没有错,错的倒是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。
这就是要算历史帐。而毛泽东的道理也很简单:王明要算历史帐,那就算历史帐。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灭顶之灾,你王明竟连一句反省都没有,你倒是有了理了?
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?难道是书本吗?难道离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,空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,就可能标榜自己代表马克思主义了吗?
于是,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——即他后来所说的“党书”,他把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,编订成册,而这就是《六大以来》。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:“在编辑过程中,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——两条路线问题。”
1941年9月10日至12月22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,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,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9月会议”。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,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,鉴于惨痛的教训,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,在那次会议上,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。
与王明不同,洛甫是明智的,洛甫明白:王明要算账,这完全是自取其辱,1942年1月26日,张闻天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,率“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”下乡去了。
延安整风确实是从“算账”开始的。但“整风”不是算个人的小账,“整风”是算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几十年中国革命史的大帐。1940年以来,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历史帐,一本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帐,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、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帐,而逼着毛泽东算账的,一个是蒋介石,另一个就是王明。
那时的毛泽东,在思索着鸦片战争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,那时的毛泽东,更在思索着五千年中国历史。中华民族如果不是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灭亡,那就必须建立起朴素的政治,朴素的文明。毛泽东说,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”和“实事求是”,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两个根本点,而文明的实质就是“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”。这也就是说,所谓文明绝非形式主义的文辞,文明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、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。正是基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这种理解,毛泽东更为分别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“敏”与“讷”。
中国共产党自创党以来,就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,很长时期以来,党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了圣旨,从大革命时代的依靠资产阶级,放弃革命的领导权,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”,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,这种忽左忽右,使中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“秧歌政权”,更使党经历了极为惨痛的失败,而其根源就在于,党没有思想和理论的自信,党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自主性。近代中国丧失独立性,这不仅是物质上的,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。反映在党内,这就集中体现为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对于党的统治。
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,就是迷信外国、迷信洋人,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实状况在党内精神生活上的反映,它集中表现为党内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,而把中国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。毛泽东说:
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,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。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,对于自己的祖宗,则对不住,忘记了。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,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。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,或懂得甚少,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,真正懂得的很少,近百年的经济史,近百年的政治史,近百年的军事史,近百年的文化史,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。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,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,也是可怜得很,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。
几十年来,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。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,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。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,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。这种毛病,也传染给了共产党。
中共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,还保留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切缺点。而在毛泽东看来,士大夫阶级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,所谓理论脱离实际、生活脱离群众,八股文风,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痼疾。中华民族欲求自新,欲求真正之解放,就必须批判地总结自己的历史,批判地总结自己的文明。
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,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,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。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反思,绝非局限于明代一隅,更不是局限于儒家一门。而毛泽东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,也非一切“大儒”的学术所能涵盖。毛泽东的思索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,上下五千年,包纳华夏与四夷。
毛泽东说,我们的历史上有糟粕,但也有精华;有腐败,但也有朴素;有黑暗,但更有光明。历史虚无主义是站不住脚的,真正问题在于能够正确区分,究竟哪是糟粕、腐败和黑暗,哪是精华、朴素与光明。在我们的历史上,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这是中国的脊梁。
毛泽东最后这样总结说:
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,这三种东西,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,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,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。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,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。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,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,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,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。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,如果不加以节制,不加以改造,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,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,或党八股。
1942年,面对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,面对着中华民族的空前危亡,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指出了再造文明,重整乾坤的道路,他的出发点,就是造就一支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先锋队,而造就这样一支先锋队,那就必须从改造我们的学习、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入手。
只有懂得了中国历史,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整风。只有懂得什么是文明,才能真正明白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意义。
只有懂得了什么是朴素的政治、朴素的文明,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那首最著名的词:
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
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
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
须晴日,看红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
江山如此多娇,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
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;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。
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。
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
1943年3月20日,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,中央书记处主席,连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。毛泽东第一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。那一年,他50岁。
7月8日,王稼祥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》,第一次正式、公开提出“毛泽东思想”,文章指出: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——过去现在与未来——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,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。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,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,中国的共产主义。
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,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,就夺取了全中国。(编辑 季节)